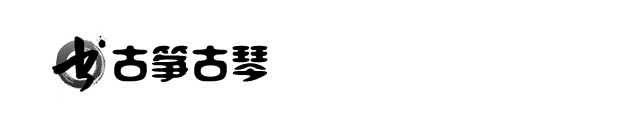我叫沈然,今年二十岁,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学生。如果说我身上有什么不普通的地方,那大概就是我的“床”。

这件事,在我的老家,槐树村,几乎无人不知。村里人看我的眼神总是混杂着同情、恐惧和一丝难以言喻的古怪。大人们会告诫自家小孩离我远点,说我身上阴气重,沾染了会生病。
我的童年,几乎没有朋友。唯一的玩伴,就是村头那棵据说有上百年历史的老槐树,以及躺在我房间里,那口安静的棺材。
棺材的尺寸是爷爷量着我当时的身高打的,但又留足了余量,仿佛算准了我长大后的个头。内里铺着厚厚的棉絮,上面是奶奶缝制的棉布床单,绣着几朵不知名的黄色小花。除了形状怪异,躺在里面其实很舒服,冬暖夏凉,而且格外安静。只要盖上棺材盖——当然,盖子内侧被爷爷凿了几个不起眼的通气孔——外面世界的喧嚣便与我隔绝。
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意外去世了,是爷爷奶奶把我拉扯大的。奶奶在我四岁那年也走了,从那以后,我和爷爷相依为命。
爷爷是村里远近闻名的木匠,一手手艺出神入化。小到板凳桌椅,大到婚嫁的木箱、祝寿的匾额,只要经他的手,无一不是精品。但他一生最得意的作品,不是那些为人称颂的家具,而是给我打的这口棺材。
五岁那年的夏天,格外炎热。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,仿佛要把整个夏天的生命力都喊出来。而我的爷爷,却在那年夏天迅速地衰败下去,像一棵被抽干了水分的老树。
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,爷爷的房间里总是弥漫着浓重的中药味。他不顾自己的身体,几乎把所有清醒的时间都花在了后院。那里堆满了他精挑细选来的阴沉木,木料乌黑,质地坚硬,沉水不腐。村里人说,这是做棺材最好的料子,能保尸身千年不坏。
“然然,过来,让爷爷量量。”他总是带着慈祥的笑,用那双布满老茧和木屑的手,仔仔细细地测量我的身高、肩宽。
他的咳嗽越来越重,身体也越来越佝偻,但手里的斧子、刨子却依旧稳健。木屑纷飞中,一口精致的棺材雏形渐显。它没有普通棺材的沉重和阴森,线条反而有些柔和,上面还雕刻着一些我看不懂的繁复花纹,像是某种符文,又像是某种古老的图腾。
我记得很清楚,棺材完工的那天,爷爷把我拉到身边,指着棺材,前所未有地严肃。
爷爷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难明的情绪,有不舍,有担忧,但更多的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。他摸着我的头,一字一句地说道:“对别人来说,这是终结。但对你来说,这是开始。它能保你平安长大,能替你挡灾避祸。你记住,无论发生什么,每晚都必须在里面睡足六个时辰(12小时),日出方可出。在你二十岁生日前,绝不可在外留宿过夜,一次也不行!你……能答应爷爷吗?”
得到我的承诺,爷爷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,整个人都瘫软下去。三天后,他躺在自己的床上,安静地走了。
葬礼上,我没有哭得撕心裂肺。因为每天晚上,当我睡在爷爷为我打造的这口“长生屋”里时,闻着那熟悉的楠木香,就好像爷爷从未离开。
爷爷走后,我成了孤儿。村委会接管了我的生活,靠着政府的补贴和村民们时有时无的接济,我磕磕绊绊地长大了。
每个夜晚,我都睡在里面。一开始,村里负责照顾我的张婶还试图劝说我,想把那口“不吉利”的棺材给扔了,给我换张新床。但我的态度异常坚决,甚至不惜用绝食来抗议。几次三番后,他们也只好由我去了。
在学校里,因为我的“怪癖”,我成了被孤立的对象。同学们背地里叫我“棺材仔”,当着我的面指指点点。我没有朋友,总是独来独往。
因为我有一个他们都不知道的秘密。睡在这口棺材里,我能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宁。我的睡眠质量极好,从不做噩梦,精力也总是比同龄人旺盛得多。15年来,我甚至连一次感冒发烧都没有过。身体好得不可思议。

有时候,在深夜里,我能感觉到棺材的木质纹理中,似乎有一股微弱而温暖的气流,缓缓地包裹着我,像爷爷温暖的手掌。
我也曾好奇过,爷爷为什么要我这么做。他雕刻在棺材上的那些奇怪符文,到底是什么意思?我试着去查过一些资料,但一无所获。那些花纹不属于任何已知的文字或符号体系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考上了县城的高中,离开了槐树村。为了方便,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,第一件搬进去的家具,就是那口沉重的阴沉木棺材。
房东第一次见到的时候,吓得差点把租金退给我。我费了好一番口舌,编造说这是家族的某种行为艺术或是纪念祖先的特殊方式,并且加了些钱,他才半信半疑地同意了。
高中三年,大学一年,我始终恪守着和爷爷的约定。无论多晚,无论什么情况,我都会回到我的“长生屋”里度过漫漫长夜。
他是个地道的城里人,阳光开朗,热情得像个小太阳。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因为我的沉默寡言而疏远我,反而主动地靠近我,约我一起打球,一起去图书馆。是他,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同龄人的友谊。
我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友谊,但关于棺材的秘密,我依旧守口如瓶。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,我怕他会像其他人一样,用看怪物的眼神看我,然后离我而去。
大二上学期的这个周末,王磊的父母出差去外地,他邀请我去他家住,说是可以一起通宵打游戏,完成小组的课程设计。
“来吧,沈然!我家大得很,客房早就给你准备好了!咱们正好把那个烦人的模型给做了!”他搂着我的肩膀,热情地发出邀请。
“别啊!”王磊不依不饶,“你太孤僻了,就当陪陪我嘛。再说了,我们那个小组作业不是快到截止日期了吗?在我家做,资料又全,网速又快,多方便啊!”
看着他真诚期待的眼神,拒绝的话哽在我的喉咙里,怎么也说不出口。他是我的第一个朋友,我不想让他失望。
而且……我已经快二十岁了。15年过去了,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或许,这只是爷爷出于对我的过度担忧,而想出的一个有些极端的方法?毕竟,他只是个普通的木匠,不是什么神仙道士。也许,只是一个善意的迷信罢了。
王磊家住在市中心一个高档小区,房子是视野开阔的大平层。他父母虽然不在,但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。
我们一起吃了外卖,喝了点啤酒,然后便一头扎进了课程设计里。不得不说,王磊家的设备确实齐全,我们俩合作,效率出奇地高。不知不觉,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。
午夜时分,我们终于完成了设计的主体框架。王磊打了个大大的哈欠,伸着懒腰说:“不行了不行了,我得去睡了。客房在那边,床单被褥都是新换的,你随便用啊。”
这是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感觉。就好像……一个一直穿着盔甲的士兵,突然被剥光了所有防护,赤裸地暴露在危机四伏的战场上。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某种看不见的危险因子,让我浑身不自在。
我躺在柔软的大床上,翻来覆去,却怎么也睡不着。没有了那熟悉的楠木香,没有了那密闭空间的包裹,我感觉自己像是漂浮在无垠的大海上,随时可能被一个浪头吞没。
梦里,我又回到了槐树村的老屋。爷爷就站在我的面前,还是我记忆中最后的样子,瘦削而苍老。但他脸上的神情,却不是我熟悉的慈祥,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,极致的惊恐和焦急。
他的嘴唇在不停地翕动,似乎在对我呐喊,但我却听不到任何声音,只能看到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,充满了血丝和绝望。

一声炸雷般的呐喊,猛地在我脑海中响起。我陡然睁开眼,心脏狂跳不止,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。
房间里一片漆黑,只有窗帘的缝隙里透出城市夜晚诡异的霓虹光。我还沉浸在梦境带来的巨大恐惧中,大口地喘着粗气。
那不是一个普通的梦。爷爷的眼神太过真实,那份绝望和惊惶,仿佛要穿透梦境,烙印在我的灵魂上。
我的目光下意识地,缓缓移向了窗边。鬼使神差地,我掀开被子,赤着脚,一步步地走了过去。我的手在颤抖,但我还是轻轻地,拉开了窗帘的一角。